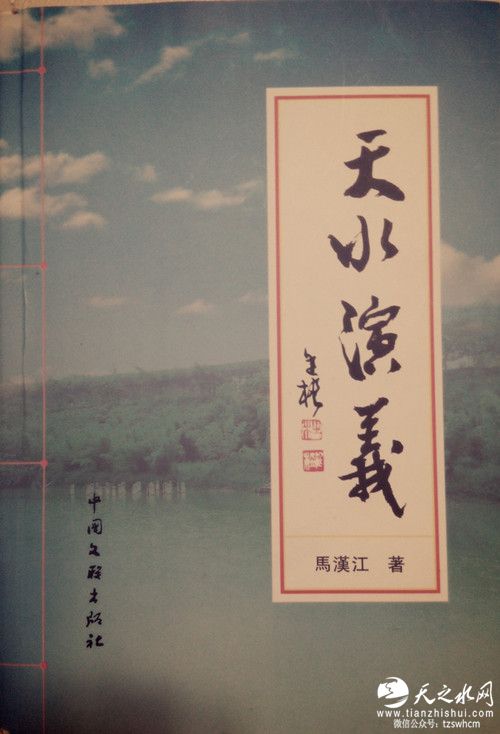
風(fēng)味獨(dú)具的地方史話
——津門夜讀《天水演義》札記
秦嶺
一部《天水演義》,像天水雜燴,熱氣騰騰地到了我津門的案頭。
這是年近古稀的天水人馬漢江老先生從歷史隧道里分離出來(lái)又熬制而成的味道,古老而新鮮,糅雜著大地、莊稼和灶臺(tái)的氣息。中國(guó)人回望歷史是有難度的,不僅因?yàn)橹袊?guó)的歷史斷層阻隔、游弋不定甚至面目全非,而且存在“今人寫(xiě)古”的歷史觀和切入方法問(wèn)題。如何演義好天水這片擁有8000年文明史的中華民族的重要發(fā)祥地,首先考驗(yàn)的是今人的精神姿態(tài),這一關(guān),誰(shuí)敢打馬靠前?
“人皇提地始天水,山河鐘秀最宜居”。馬漢江就這樣義無(wú)反顧地開(kāi)場(chǎng)了,老先生分明以理性和感性兼容的頑強(qiáng)姿態(tài),策馬關(guān)前,吆喝叫陣。他的戰(zhàn)略與戰(zhàn)術(shù)既遵循了傳統(tǒng)陣法,同時(shí)又土洋結(jié)合,形成了自己獨(dú)特而實(shí)用的完勝路徑,于是,我們從長(zhǎng)達(dá)30章30萬(wàn)字的《天水演義》里,感受到了歷史的家長(zhǎng)里短和有別傳統(tǒng)的宏觀敘事。全文以創(chuàng)世以來(lái)的天水歷史為主線,自三皇之首伏羲始,至共和國(guó)成立終,張弛于華夏的歷史長(zhǎng)河與天水的盤(pán)根錯(cuò)節(jié)之間,家國(guó)風(fēng)云,盡收眼底;文本結(jié)構(gòu)采用的是中國(guó)傳統(tǒng)章回小說(shuō)之法,每回每章以“詩(shī)曰”啟幕,以“且聽(tīng)下回分解”轉(zhuǎn)呈,但作者在小說(shuō)堡壘的縫隙中,像給土坯灌漿一樣輸入了紀(jì)實(shí)、文獻(xiàn)、傳說(shuō)、掌故、野史元素,為讀者拓展了多元思考與想象的空間;故事脈絡(luò)的梳理使用的是傳統(tǒng)敘事方式,卻巧妙地把歷史事件、歷史人物整合起來(lái),以講故事為主,又輔之判斷分析,凸顯了文本的史料性和參照價(jià)值;在材料的取舍和故事的鋪設(shè)中,作者顯然以史為由,抓主抓重,去偽存真,同時(shí)不忘廣泛搜集、甄別、梳理歷史的異聲、質(zhì)疑、紛爭(zhēng)和流傳與民間麥垛、炕頭的文化信息,在真與假、詳與略、繁與簡(jiǎn)、重與輕、厚與薄、寬與窄中,想方設(shè)法抵達(dá)自己的講述目標(biāo);章回?cái)⑹轮螅S附四篇與天水作為我國(guó)縣制肇始之地、街亭古戰(zhàn)場(chǎng)有關(guān)的學(xué)術(shù)論文,可謂錦上添花。作者不僅讓我們重溫了伏羲、女?huà)z、軒轅、秦非子、李廣、姜維、段會(huì)宗、李淵、李白、隗囂、苻堅(jiān)、趙壹、上官婉兒、蘇若蘭等燦若群星的天水兒女的文史面貌,感受了一畫(huà)開(kāi)天、非子牧馬、六出祁山、失街亭等重大歷史事件的遠(yuǎn)古回聲,而且對(duì)隴東南大地的仇池、西垂、大地灣、大堡子山、麥積山、伏羲廟等星羅棋布的歷史遺存有了更為立體的、生活化的認(rèn)知。這是馬漢江的智慧,也是《天水演義》的力量。
我不否認(rèn)為文的標(biāo)準(zhǔn),《天水演義》的價(jià)值恰恰無(wú)法用既定或庸常的標(biāo)準(zhǔn)來(lái)衡量,馬漢江走的是大眾化、通俗化的路數(shù),而指向卻是奔史學(xué)的普及、常識(shí)的辯證、文化的呼喚去的。它對(duì)故事的解構(gòu),對(duì)主副線的埋設(shè)與綻放,始終在跨文體、越疆界中有序運(yùn)行,并力求通過(guò)夾敘夾議、查缺補(bǔ)漏、前行后溯為敘事圓場(chǎng),樸素而直觀地體現(xiàn)了雅俗共賞的審美特質(zhì)。你可以用小說(shuō)、志書(shū)、百科、史料的角度去審視,卻無(wú)法選其一強(qiáng)行規(guī)范和歸類。作者清醒自己的局限和演義的門檻,因而有拙不藏拙,有瑕不掩瑕,有短不護(hù)短,他在告訴你:我馬漢江親手烹飪的這桌菜,有的好看,有的好吃,有的可能火候不到,有的可能姜重了鹽淡了,這都不要緊,要緊的是讓你吃個(gè)肚兒圓,其色其味,大家一起慢慢咂品,品出個(gè)啥便是啥。能嘗能品,必然碗底有肉,沒(méi)多的,有少的。
我沒(méi)見(jiàn)過(guò)馬漢江先生,當(dāng)《天水演義》通過(guò)天津師大的一位教授和天津作家肖克凡輾轉(zhuǎn)到我書(shū)房的時(shí)候,這種傳遞方式足以讓我驚異,一如我驚異這位只有小學(xué)文化程度的、有過(guò)逃荒要飯經(jīng)歷的、從鄉(xiāng)間進(jìn)入城市的“泥腿子”何以編著、創(chuàng)作了《秦源記事》、《中國(guó)朝代交替簡(jiǎn)史》、《論古詠今》等諸多著述,我不好妄論這種原動(dòng)力是否來(lái)自家國(guó)情懷,但發(fā)酵于作者骨髓的歷史和鄉(xiāng)土情結(jié)肯定是存在的,其背后的艱辛、勞頓與堅(jiān)守,可想而知。天水一隅的西漢水流域是作者老家,那里毗鄰秦始皇先祖秦襄公等諸公的皇陵,那里的風(fēng)中傳遞著《詩(shī)經(jīng)》時(shí)代的農(nóng)事民情。那些閃耀在地埂之間、屋檐之上、碌碡之下的厚重而神秘的秦早期文化信息,對(duì)作者信念、立場(chǎng)、性格和精神的滋補(bǔ)是不言而喻的。馬漢江在后記中云:“回報(bào)故鄉(xiāng)養(yǎng)育之情,唯有《天水演義》一本。”讀來(lái)為之動(dòng)容。有良知的讀者一定能感受到一位歷史老人的傳統(tǒng)文化基因和學(xué)術(shù)態(tài)度,體會(huì)到一位地方文化人的民間視野和矢志不渝的鄉(xiāng)土情懷。有意思的是,很多居廟堂之高者以及象牙塔里的所謂知識(shí)精英,反而未必具備這一點(diǎn)。馬漢江的勇氣和方法,令人扼腕。
電話得知,先生沉疴在身仍筆耕不輟。其為文之道,實(shí)可道也!
2015年10月7日于天津觀海廬



已有0人發(fā)表了評(píng)論